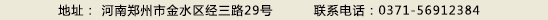没时间读毛姆这两篇就够了
读毛姆的短篇,别的没什么,
答应我一定要看《午餐》和《逃脱》。
两篇都很短,但是特别微妙,
结尾都是神来之笔,拐弯抹角的嘲讽,看完忍不住偷笑。
《逃脱》告诉我们促使情侣尽快分手的最好方法是装修买房。
而《午餐》则说明,无论如何,
你吃过的饭都会以体重的方式反映在你身上。
逃脱
我一向坚信,一旦哪位女士下决心要嫁给一个男人,那么,能使这个男人幸免于难的唯一方法是立即逃之夭夭。其实也不尽然。比如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阴影向他逼近时,就从一个港口乘船而逃(他的全部行装就是一把牙刷,因为他太清楚他面临的危险和立即行动的必要性了),他在世界各地周游了一年,然而,当他感觉平安无事之后(据他说,女人都是水性杨花的,不出十二个月她就会把你忘得一干二净),在他出走的那个港口登陆时,他看到的头一个人,那个兴高采烈地在码头上向他招手的人,正是他甩脱了的那位小妇人。只有一次我知道有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想法逃出了罗网。他的名字叫罗杰·查林。在他爱上露丝·巴罗的时候,他早已经不是个年轻人了,因此他有丰富的经验,叫他谨慎从事。然而露丝·巴罗却有一种天赋(或者称之为一种特质?)可以使大多数男人俯首就范。正是这种才能剥夺了罗杰所具有的常识、谨慎和世故。他像九柱戏里的那排柱子一样被打倒了。巴罗太大的才能是善以哀婉感人。巴罗太太——因为她已经守寡两次——生着一双非常漂亮的黑眼睛,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动人的眼睛。泪水好像随时会从这双眼睛里夺眶而出。从这双眼睛里你可以看出,这个世界对她来讲是太残酷了。你能感觉到,这个可怜的人儿,她所经历的苦难是其他任何人也没有经历过的。假如你像罗杰·查林那样,是一个坚强有力而又非常阔绰的人,那么,你毫无疑问会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挺身而出,站在生活的苦难和这个无依无靠的小人儿中间保护她。呵,要能从这双又大又可爱的眼睛中去掉那种悲伤的神色该多么好啊!我从罗杰的话里听出来,所有的人都欺负巴罗太太。她显然是那种事事全不顺心的倒霉人儿。要是她嫁了人,丈夫准打她;要是她和掮客打交道,人家准骗了她;要是她雇个厨子,那家伙免不了也是个酒鬼。她所珍贵的东西,没有一样能保存得长久,哪怕是一只小羔羊,也早晚非死不可。 当罗杰告诉我说他终于说服巴罗太太和他结婚时,我祝愿他幸福。 “我希望你们也能成为好朋友,“他说,”她有点儿怕你,知道吗?她觉得你这个人冷冰冰的。” “说真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你是非常喜欢她的,对吗?” “非常喜欢。” “她有一段痛苦的经历,可怜的人儿,我真是太同情她了!” “是啊。” 我的回答不能比这更简短了。我知道她很愚蠢,而又觉得她很有心计。她在我心目中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我第一次遇见她时,我们一起打桥牌。在她跟我一家时,她两次打掉了我最大的牌。我却表现得像天使一样。不过应当承认,我当时想过,如果有人该流眼泪的话,与其说是她不如说是我。而且到晚上打牌时,她输了我一大笔钱,她说以后会寄给我一张支票,可是我到一直也没收到。我不禁想到,下次我们见面时,要摆出一副苦相的,肯定是我而不是她。 罗杰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他送给她很多名贵的珠宝,不论他到什么地方去都要带着她。他们宣布说最近就要举行婚礼。罗杰非常幸福。这真是一举两得:他做了一件好事,同时又是一件他求之不得的事。这种情况可不常见,而且,如果说他稍微有一点得意忘形的话,那也不足为奇。 然而,忽然间,他的爱情终止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可能是因为他厌倦了和她谈话,因为她根本就不怎么会说话。也许仅仅是因为那忧伤的外表停止波动他的心弦了吧?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开来。他又一次像过去那样老于世故了。他敏锐地意识到,露丝·巴罗是下了决心要嫁给他。他郑重地起誓说任什么也不能使他和露丝结婚。开始他又感到进退两难。现在,由于头脑非常冷静,他清楚地了解他所要应付的是怎样一个女人。他明白,假如要求她解除婚约,她会(以诚恳的方式)为她受伤害的情感索取高价的报酬。除此之外,甩掉一个女人会使男人的处境非常尴尬:人们往往觉得他这样就是品行不端。 罗杰将自己的计划埋在心里。他不论从言谈上还是举止上都丝毫不露出他对露丝的感情已产生变化的迹象。他还是尽量满足她的全部愿望,还是常常带她下饭馆,一起去看戏,给她送鲜花;他对她体贴入微,温柔备至。他们决定,只要找到合适的房子就立刻举行婚礼,因为他现在还住在单身房间里,而她也还住在公共寓所里。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他们渴望得到的住宅。房屋经理人一给罗杰送去一批房单,他就是带着露丝一起去看看这些房子。要想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房子是非常困难的。罗杰又向更多的房屋经理人提出了申请。他们一幢接一幢地看过这些住所,检查得非常仔细,从房子底层的地窖一直看到房檐下的阁楼。这些房子有的显得太大,有的又太小;有的离闹市区太远,有的又太近;有的房钱太贵,有时房子又过于破烂不堪;有时太憋闷,有时又太透风;有时太阴暗,有时又太空旷。罗杰总能挑出一点毛病说房子不合适。当然,他是不容易满足的:除非是十全十美的房子,否则他绝不忍心让他心爱的露丝住进去,而十全十美的房子还有待发现。找房子是一件令人疲倦和厌倦的事儿。露丝很快就开始发脾气了。罗杰恳求她耐住性子:毫无疑问,他们所寻求的那种房子一定是有的,只要稍稍坚持一下就一定会找到。他们挑过成百上千的房子,爬过成千上万阶楼梯,察看过数不清的厨房。露丝被搞得精疲力竭,不止一次大发雷霆。 “如果你不能很快找到一幢房子,”她说,“我只好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哼!要是这样下去,我们再过多少年也没法儿结婚。” “别这么说,”他回答,我希望你要有耐心。我刚从新的联系上的房屋经理人那里收到一批新房单。这一批至少有六十幢房子。“ 他们又开始去追寻。他们又察看了更多更多的房子。有两年时间他们一直在找房子。露丝变得沉默寡言而且爱发牢骚了。她那伤感而美丽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几乎是阴沉沉的神色。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巴罗太太有着天使一样的耐心,可是最后她也反叛了。 “你到底打不打算跟我结婚?”她质问他说。 她的声音里含着一种不常出现的严厉。尽管如此,罗杰在回答时仍然是温文尔雅的。 “我当然想和你结婚。只要找到房子,我们立刻举行婚礼。顺便说一下,我刚听说有所房子可能对我们很合适。” “我没有兴致再去看什么房子了。” “可怜的人儿,我怕你是有点疲倦了吧?” 露丝·巴罗整天躺在床上不出门了。她不愿意再见罗杰。他呢,只好给她住所每天去电话问候,不断地送去一些鲜花。他像以往一样地殷勤周到、曲意温存。每天他都要写信告诉她说又打听到有另一批房子值得他们去看一看。一个星期过去之后,他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罗杰: 我认为你并不是真心爱我,我已经找到一个愿意照料我的人,而且我今天就要和他结婚了。 露丝。 他派专人送去了回信: 露丝: 你送来的消息使我痛不欲生。我永远也无法从这一打击下恢复过来。然而,你的幸福当然是我要首先考虑的事情。随信附上七份房单,请阅。这是今天早晨刚邮来的。我敢担保,在它们当中你一定能找到一所完全合你心意的房子。 罗杰。
午餐
我是在剧场看戏时见到她的。她向我招了招手,我趁幕间休息的时候走了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还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不是有人提过她的名字,我想我这次就认不出来她了。她满面春风地和我拉扯起来:
“哦,好多年没见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也都老了。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吗?你邀请我去吃了一次中饭。”
我怎么能不记得。
那是二十年之前的事了,当时我住在巴黎。我在拉丁区有一间小小的公寓,从窗里可以俯瞰教堂的墓地。我的收入刚好够维持住我的灵魂和躯壳不分家。她读了一本我写的书,给我写了封信谈论这本书。我回信表示感谢。过了没多久我就又收到她一封信,说她要路经巴黎,想同我谈谈;不过她的时间有限,只能在下星期四抽出点空来,早上她要去卢森堡公园,问我是否愿意中午请她在福约特餐厅随便吃点什么。福约特是法国议员们经常光顾的一座餐厅。它远远超出我的经济能力,所以我从来不敢问津。但是她信中的恭维话说得我心头发痒,而且那时我太年轻,还没能学会对一位女士说“不”。(我不妨加一句,没有几个男人学会拒绝女人。等到他们学会对女人们所说的话认为无足轻重时,年纪已经太老了。)我还有八十个法郎(金法郎)可以维持月底之前的开销。一顿便餐不会超过十五个法郎。如果我后半月不喝咖啡的话,我没准可以对付过去。
我回信和我这位朋友约好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半在福约特餐厅见面。她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年轻。她的外表与其说风姿动人毋宁说富态魁梧。实际上她已经有四十岁了(一个颇能迷惑人的年纪,但不是一眼就可以使你激动和产生强烈情感的年龄),她给我的印象是她的牙齿比实际需要多了一些,整齐、洁白、比较大。她很善谈,但因为她好象倾向于谈论关于我的事,所以我准备好做一名专心致志的听众。
菜单拿上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价钱比我预料的要贵得多。但她说的话叫我放了心。
“我中午从来不吃什么,”她说。
“哦,可不要这么说!”我慷慨大方地回答。
“我只吃一道菜。我觉得现在人们吃得太多了。也许我可以来点鱼,我不知道有没有鲑鱼。”
吃鲑鱼的季节还略嫌早了一点,菜单上也没有写着这道菜。但是我还是问了一下侍者。有,刚刚进了一条头等鲑鱼,这是他们今年第一次进这种货。我为我的客人叫了一份。侍者问她在等着烹制鲑鱼的时候是否吃点别的。
“不,”她回答,“我中饭只吃一道菜。除非你们有鱼子酱。吃点鱼子酱我倒不反对。”
我的心微微一沉,我知道我吃不起鱼子酱,但我无法对她讲明这点,结果我还是吩咐侍者拿了份鱼子酱。我为自己挑了一份菜单上价格最便宜的菜——一份肉排。
“我认为你吃肉可并不明智,”她说,“我不知道你在吃完象肉排这类油腻的东西以后还怎么能工作。我可不能叫我的胃负担过重。”
这以后出现了饮料问题。
“我中饭从来不喝什么酒,”她说。
“我也如此,”我迫不及待地补了一句。
“除了白葡萄酒,”她继续说道,仿佛没听到我刚才的话。“法国白葡萄酒一点儿也不厉害,对消化很有帮助。”
“你想喝点什么?”我依然殷勤地问道,但已不那么曲意逢迎了。
她的一口洁白的牙齿一闪,对我殷勤地笑了笑。
“除了香摈我的医生绝对禁止我喝其它的酒。”
我想我的脸当时一定变得有些苍白。我叫了半瓶。我用随便的语气提到我的医生不允许我喝香摈。
“那么你喝什么?”
“水。”
她吃掉鱼子酱。她吃掉鲑鱼。她谈笑风生地谈论艺术、文学和音乐。可我却一直琢磨账单加起来会要我多少钱。当我那份羊排端上来时,她非常严肃地教训我。
“我看得出来你习惯中饭吃得很多。我认为这肯定不好。为什么你不学学我只吃一道菜?我肯定这对你会大有好处的。”
“我是只吃一道菜。”我说道,这时侍者又带着菜单来了。
她手一挥把他打发到一边去。
“我可不这样,我中饭从来不吃什么,吃也只吃一点,吃这点也是为了聊天方便。我可再也吃不下什么了------除非那种大龙须菜。如果不尝尝的话,这次到巴黎来可是件憾事。”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在橱窗里见到过龙须菜,我知道这东西贵得要命。我的嘴巴也常常因为看到它们而馋涎欲滴。
“夫人想知道你们有没有龙须莱,”我问侍者。
我捏着把汗真希望他说没有,一个快乐的笑容掠过了侍者的神甫似的大脑。他对我说他们有一些那么大,那么好,那么嫩的龙须莱,简直绝无仅有。
我叫了一份。
“你不要吗?”
“不要,我从来不吃龙须菜。”
“我知道有人不喜欢龙须莱。事实是你吃的那些肉把你的胃口破坏了。”
我们等着龙须菜上来。我吓得心惊胆战。现在已经不是我可以剩下几个钱过日子的问题了,而是我是否有足够的钱拿出来付账。如果发现自己缺十个法郎不得不向客人张口的话,那就太叫人丢脸了。说什么我也不能丢这个丑。我清楚地知道我有多少钱,如果不够付账的话我下决心把手往兜里一伸,然后戏剧性地大喊一声,跳起来说我被扒手扒了。当然了,那将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场面,如果她也没有足够的钱付账的话。要是那样,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留下我的表作抵押,过后再来赎了。
龙须菜上来了,又大又粗,一咬一汪水,真吊人胃口。它那嗞嗞作响的奶油香味一阵阵地往我鼻孔里钻,就象耶和华嗅到虔诚的希伯莱人奉献上烤得香喷喷的供品时一个滋味。我一边望着这位纵情大嚼的女人一大口一大口地往嗓子眼里塞,一边客客气气地谈论着巴尔干半岛的戏剧界现状。她终于吃完了。
“咖啡?”我问道。
“好吧,一客冰激凌加咖啡,”她回答。
我现在已经把一切置之度外了,我给自己也叫了咖啡,给她要了冰激凌加咖啡。
“你知道,我是相信这个真理的,”她边吃冰激凌加咖啡边说,“一个人吃饭时—定要只吃八成饱。”
“你还饿吗?”我有气无力地问道。
“哦,不饿了;你看,我中午不吃饭。早上我喝一杯咖啡,之后就吃晚饭了。中饭我至多只吃一道菜。我这也是在劝你。”
“说得是,我一定听从你的劝告。”
之后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当我们等着咖啡的时候,领班侍者摆着一副讨好的笑容向我们走来,胳膊上挎着一满篮子大桃,红得好象纯洁的姑娘的脸蛋,色调有如意大利绚丽的风景画。桃子肯定还没有到上市的季节。只有上帝知道多少钱一个。我也知道了——那是在过了一会儿以后,因为我的客人一边继续谈话,一边心不在焉地随手拿了一个。
“你看,你用肉塞满了肠胃,”——她指的是我那一块可怜的肉排——“你什么也吃不下去了。而我只随便象吃点心一样地吃了点,我还可以享受个桃子。”
账单来了,付完帐后我发现剩下的钱不够一次象样的小费。她的目光在我留给侍者的三个法郎上停留了片刻,我知道她一定想我很吝啬。但是我在走出饭馆后,带着一张嘴和一个肚子,但口袋里却一文不名。
“学我的样子,”在我们握手道别时她说道,“中饭千万只吃一道菜。”
“我会比这做得还好,”我大声回答,“今天晚饭我就什么也不吃了。”
“幽默家!”她快乐地喊着,跳上了一辆马车,“你真是一个十足的幽默家!”
但我终于复了仇。我不认为我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可是当不朽的大神插手这件事时,你暗自得意地看到这个结果也还是可以原谅的。今天她体重三百磅。
钱塘潮涌,做温暖的人,写生动的字,愿在阅读中与您分享生命的喜怒哀乐!(长按白癜风治疗白癜风怎么治疗
转载请注明:http://www.meijiangwang.com/lxcxg/8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