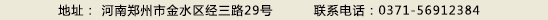卡拉姆辛俄国旅人信札片段
?作者简介:
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卡拉姆辛(一),俄国作家、历史学家。地主家庭出身。-年就读于莫斯科寄宿中学,同时在莫斯科大学旁听。一生主要从事著述,深受法、德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但主张温和的保守主义,寄希望于在俄国开展文化启蒙运动,实行开明君主制。-年游历西欧归来,创办文学月刊《莫斯科杂志》(-),发表《俄国旅人信札》、小说《革命的丽莎》()等名篇,还大量翻译和评介了斯特恩、卢梭等英法感伤主义作家的作品,成为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年间主编文学和政治半月刊《欧罗巴导报》。年起全力撰写十二卷本的《俄罗斯国家史》,首次完整而生动地叙述了从远古至17世纪的俄国历史。
在文学体裁和文体风格方面,卡拉姆辛主张打破古典主义的“三种文体”的严格界限,提倡各种体裁和文体的交互并用和相互渗透,强调提高散文作品的地位,改变重诗轻文的局面,尤其注重发挥小说和游记的作用。他的散文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轻灵生动,通俗易懂,深受当时读者的喜爱。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卡拉姆辛第一个在俄国用社会的生动语言代替僵死的书面语言”。
?编者按:
本文选自《俄国经典散文》。虽然作者卡拉姆辛的作品至今尚没有中译全本,所见到的文字零零散散地收录到几个群作家的作品选集之中,但这并不是说卡拉姆辛的文字太过乏味,人所共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阅读史里便有意地提到了卡氏的《俄国史》,我自己读到本篇文章的时候,老实说,一开始是无聊的,但顺着读下去,又像是尾随着作者的脚步穿越到那个时代的种种现场,颇有些畅快淋漓之感。读毕,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留恋之情。个人认为,汉译界到现在还没有卡氏的作品全译本,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特威尔里,年5月18日
我和你们离别了,亲爱的人们,离别了!我的心以无限柔情眷恋着你们,但我却正远离你们而去,而且是愈离愈远了!
心儿啊,心儿!谁能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多少年来我梦寐以求的最大的乐事不就是旅行吗?我不是曾欣喜若狂地自言自语说:你终究成行了?我不是每天早上都高高兴兴地醒来?不是一想到“你就要走了”就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有多少时日了,我除了旅行,什么事都不想,也不做?我不是曾经逐日逐时地计算过时间?但是——当这朝思暮想的日子到来时,一想到我要和世界上与我至亲至爱的人们分别,和那可说是构成我精神存在的一切分别的情景时,我竟黯然神伤了。那张书桌,几年来我一直在它上面把我不成熟的思想和感情倾吐在纸上;那扇窗户,我多少次在愁思悠悠,难以释怀时久久地坐在它旁边,直到晨光照拂我的胸前;那幢哥特式的楼房,它是我在夜里最爱凝视的对象——总之,无论我的目光投向哪里,那映入我眼帘的一切都是对我生活中已逝岁月的珍贵纪念,这生活虽没多少丰功伟绩,却充满思想和感情。我和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像和朋友一样告别。而正当我愁肠寸断,伤感万分的时候,我的仆人们来了,他们哭了起来,并请求我不要忘记他们,回来时再召他们来。亲爱的人们,眼泪是有感染力的,尤其是在这种时刻。
但我的至亲至爱还是你们,所以理当和你们道别。我心中虽有千万缕情丝,但只能默默无语。对你们能说什么呢!我将来即便有千万个欢快的时刻,也未必能补偿我与你们分别的这一时刻。
亲爱的彼特洛夫送我到城关。我们在那里相互拥抱,我还是第一次见他流泪。在那里我坐上马车,眺望了一眼留下我多少心爱之物的莫斯科,并说了声:别了!车铃响了,马儿奔跑起来,你们的朋友成了这个世界上的孤儿,自己心中的孤儿。
过去的一切都如梦似影。亲爱的人们啊,在与你们相处的时刻,我心中的感觉是多么美好,如今,去哪里追寻这些时刻?一个万事如意的人本来要称自己为芸芸众生中的幸运儿,但如果在这一时刻,他突然面临吉凶未卜的未来,他的心会由于恐惧而停止跳动,他的口舌也会顿时语塞!……
整个旅途中我始终没有过一丝欢快的思绪。在特维尔里前的最后一个驿站,我的忧伤之情竟不能自已,我站在乡间酒馆墙上挂的法国皇后和罗马皇帝的漫画前,真想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哭出我的心来。我已经告别的一切人人事事,在这里又都一一呈现出来,令我无限眷恋……我重又悲伤万分。别了,愿上帝赐福于你们。记住你们的友人吧,不过不要有一点悲伤!
哥尼斯堡,年6月19日
亲爱的朋友们,我昨天清晨七时抵此,并和同伴一起下榻于申诺克旁的一家客店。
哥尼斯堡是普鲁士首府和欧洲的一座大城市,方圆约十五俄里。曾几何时是汉萨同盟的名城之一,至今仍是相当重要的商城。城市建在普列格尔河上,河宽虽不足一百五十或一百六十英尺,但河道很深,可以航行大型商船。全城约有四千幢房屋,居民则只有四万左右——对于这么大的城市而言实在是太少了。但现在看上去人数众多,因为很多人汇集到此参加明天即将开幕的交易会。我看见许多相当漂亮的屋宇,但不及莫斯科或彼得堡的楼宇那样高大,虽然一般说来哥尼斯堡的城建比莫斯科要略胜一筹。
此地驻军颇多,所以随时可见到穿军服的人。我看普鲁士士兵的着装未必比我国士兵好,我尤其不喜欢他们戴的那种双角帽。至于军官,则仪容相当严整,所得军饷也比我国军官略多(大尉除外)。我曾耳闻,似乎普鲁士军队中没有我国军中那样年轻的军官,但我在这里至少看到过十个十五岁的军官。军服有青、蓝、绿三种颜色,上衣翻领则分红、白、橙黄色。
昨天我在大餐厅进午餐,餐厅里有年迈的少校、肥胖的大尉、魁梧的中尉、没长胡子的少尉和准尉,大约有三十来人。大家高声谈论着刚举行过的检阅,军官们的笑言戏语此起彼落。譬如:“里特梅斯杰尔先生,您如今连白天都紧闭着窗户,是什么缘故?当然绝不会是写信啰,哈,哈,哈!”“冯·克列勃斯可真不简单,我发生了什么事他全都知道!”等等。不过,他们都彬彬有礼。我们的法国小姐一露面,他们立即起身,在用餐时也对她竭尽殷勤。不过,尽管如此,下次我还是宁肯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用餐,把朝花园的窗户打开,让那里青翠欲滴的绿叶的芬芳沁人我的德国菜汤里。
昨天午餐之后,我拜访了杰出的康德,他是个思想深刻而又精细的思辨家。他既否定马勒布朗士和莱布尼茨,又否定休谟和博内。正是这个康德,被犹太族的苏格拉底,已故的孟德尔森,称做打倒一切的康德。我并未持有引荐的信函,但是志可摧城——他的房门终于向我敞开。迎接我的是位身躯瘦小,皮肤非常白皙和细腻的老者。我以这样的话开始:
“我是个俄国贵族,爱戴杰出的人物,并想对康德表示敬意。”
他立刻请我坐下,并说:
“我写的东西并不讨所有人的喜欢,喜欢精密思辨的人并不多。”
约有半小时光景,我们谈论各种话题:关于旅行、关于中国、关于新大陆的发现。他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之渊博真令人惊叹,仅仅这两方面的知识就足可把人类记忆的仓库堆满,但对他而言,用德国人的话说,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己。后来,我不无唐突地把话题转到人的本性和道德上来。下面是我记忆中留下的他的见解:
“活动是我们的使命。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满足于已经拥有的东西,并永远追求新的获取。我们总是在走向我们还想拥有某种东西的途中与死神相遇。如果你把人所想得到的一切都给他,他立刻就会觉得这‘一切’并非‘一切’。我们看不见我们此生中的目标和意愿的尽头,同时又推测那应该解开纽结的来生。对于人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愉快的,因为在此生中,在欢乐与痛苦、享乐与折磨之间没有任何均衡。我可以自慰的是我已年满六十岁,我的生命即将终结:因为我期望进入另一种更好的生活。当我回味我这一生中拥有过的种种快乐时,我并不感到快意。但当我想起我遵循内心制定的道德法则行事的那些时刻时,我觉得快乐。我说的是道德法则:我们称之为良心,对善与恶的感觉——这法则的确是存在的。我说了谎,虽然谁也不知道我说谎,但我感到羞耻。
“我们谈到来世的生活时,可能性并不显而易见,但对一切加以衡量之后,理智要我们相信这种可能。倘若我们双眼亲见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将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喜欢上它,我们就再也不能过现在这种生活,并会处于无休止的苦恼之中;否则,在我们为此岸的生活而无限苦恼时就不能安慰自己说:也许在彼岸将会好些!当我们谈到我们的使命,谈到来世的生活等话题时,我们已经假定永恒的创造性理性的存在,它服务于一切,拯救一切。拯救什么?如何拯救?……在这里,最大的圣贤都得承认自己一无所知。理性的明灯在这里熄灭,于是我们处于茫茫黑暗之中,只有幻想才能在这黑暗里遨游并创造出那不存在的事物。”——尊敬的泰斗!如果我的这些文字糟蹋了你的思想,请原谅我!
这个“打倒一切的康德”
他与拉瓦特相识,并互通信函。他说:“拉瓦特心地善良,因而十分和蔼可亲。但他的想象过于活跃,并常为幻想所惑,相信催眠术之类的东西。”我们还谈到了他的敌人。他说:“您会结识他们,并能看到,他们都是一些善良的人。”
他给我写下了他两部著作的书名,这两部书我没读过,叫《Kritikdezpractishenvernunft》和《MetaphysikderSitten》——我将把这张纸条作为神圣的纪念品保存下来。
他把我的名字记入了他的袖珍小册,并表示,但愿我的全部疑惑都已解决,然后我们相互道别。
朋友们,对这次持续了约三个小时的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谈话,我就向你们作一个这样简短的描述。康德说话很快,声音极细,且十分费解,因此我听起来很吃力,非全神贯注不可。他的居室很小,室内陈设亦不多。一切都非常简单,除了——他的形而上学之外。
7月16日,下午2时
据说,莱比锡的生活很快活——我相信此言。此地一些富商常举行午宴、晚宴和舞会。青年大学生中的花花公子们派头十足地在这些场合露面。他们打牌,跳舞,向女人献殷勤。除此之外,此地有些特殊的学术团体或是俱乐部,在这些地方人们谈论学术或政治新闻,评论书籍等等。这里也有剧院。不过,演员整个夏天都去别的城市,到秋天举行所谓的米哈依洛夫交易会前才回来。对喜欢散步的人来说,莱比锡周围有许多令人心旷神怡的去处。对嗜好口腹之乐的人,此地则有美味无比的小面包、大馅饼、龙须菜和品种繁多的水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樱桃,它既好吃,又十分便宜——买整整一碟付费不足十戈比。总的说来,萨克森生计不贵。每餐如不饮酒只要付三十戈比,房间也只要三十戈比。我在德累斯顿的开销也是这样。
几乎在每条街上都能见到几个书摊,而且莱比锡所有书商都发财——这令我颇感惊奇。诚然,此地有许多学者都需要书,但这些人几乎全都是书的作者或译者,他们购置图书时付给书商的不是钱,而是他们自己写的或译的书。此外,在任何一个德国城市都有公共图书馆,可以从图书馆借出任何书来读,只需付极少的费用。全德国的书商都来莱比锡参加交易会(每年三次:第一次始于一月一日,第二次始于复活节,第三次始于米哈伊洛夫节),并相互交换新书。有人在自己印刷厂里翻印别人出过的书,从而损害那些购买了作者手稿的人的利益,这些人被认为是不正派的人。在德国,做书的生意几乎是最重要的贸易,需要在这方面制订特殊的和严格的法律。也许,你们想知道,书商付给作者的报酬如何?视作者而定。如作者在公众中尚未有美誉,则一印张不会超过十五个银马克。但如果作者名望已高,书商可能为一印张向他支付三十、六十,甚至更多银马克。
傍晚。我如约按时来到普拉特涅尔处。
他请我入座后说:“想必您要在我们这里住一阵。”
我答道:“住几天。”
“只几天?我还以为您此来是要好好用用莱比锡。这里的学者会以促进您学术上的成就为乐事。您还年轻,又懂德语。与其在各城市之间辗转,不如在莱比锡这样的地方住下。您的许多同胞曾在这里求知,我相信,他们都没有徒劳无功。”
“博士先生,我如能做您的学生将是一大幸事,可惜有些情况,有些情况……”
“如果有些情况使您这次不能留在我们这里,我也只能遗憾了。”
他忆起库和拉及其他一些在这里求学过的俄国人。
他说:“他们都曾是我的学生,不过彼时之我还不是今日之我。”
“至少您的《警句集》那时尚未出版……”
我刚提起《警句集》,并想就某几处向他求解,有人因大学校务来访,他担任大学校长职务。
他说:“我闲暇时间不多,但您今天一定要和我共进晚餐。今晚八时,请吩咐人把您送到‘蓝天使’酒店。”
我抽空去里赫特尔花园散步(那位穿白色紧身胸衣的女郎又送给我一束鲜花),然后于晚八时来到“蓝天使”酒店。我被引进一个大房间。室内餐桌上摆了二十份餐具,但还没有一个客人。半小时后,普拉特涅尔和他的学子同仁们都来了。他把我向他们一一介绍,并对我说出他们的姓名。除了艾泽尔老教授和出版并注释过苏里泽洛夫的《艺术科学理论》一书的密勒尔先生外,所有其他人我都不认识。大家入席进餐,晚餐是典型的雅典式的,只不过饮酒不是用花编成的小杯,而是用普通的萨克森酒杯。大家都兴致很高,谈锋颇健,并希望我也加入他们的谈话,向我询问俄国文坛的情况。当我告诉他们《救世主》中已有十首译成俄语时,他们都备感惊讶。
一位年轻的诗歌教授说:“我觉得贵国的语言未必有能表达克洛卜施托克思想的词语。”
我说:“我倒要敬告诸位,俄译本非常忠实和通达。”
为了证明我国语言听起来十分顺耳,我向他们诵读了各种格律的俄国诗,他们也感受到了某种和谐。在说到俄国富有独创性的作品时,我首先举出《俄罗斯颂》和《弗拉季米尔》这两部史诗。其作者的名字理当永载俄国诗史。普拉特涅尔在席间充当主角,由他控制着谈话。一般说来,德国学者在人际交往中确有些笨拙,但普拉特涅尔博士(当然还包括许多别的人)则不在此列。他是个十足的交际场中人物:他喜欢并善于言谈,讲话爽快,源出对自己分量的自信。艾泽尔老人则以他的淳厚之风为人所亲。他备受尊敬,大家听他讲种种轶闻故事并以笑声应答,知道他想要使大家开心。叶丽莎维叶塔·彼特洛夫娜女皇在位时,他曾想访问俄国,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至于密勒尔先生,他看上去十分倨傲。十时许,大家起身,互祝晚安和告别。普拉特涅尔不让我付晚餐费,对此我并不觉得十分快意。莱比锡的学界精英们就是这样每周一次共进晚餐,并在愉快的谈话中度过一晚。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见到的这些人都是值得我尊敬的学识渊博、聪明有趣的出色人物——但他们都远离我的心灵。他们之中谁会有一丁点需要我吗?人人都忙于自已的事业,谁也不会顾念到一个可怜的游子。如果黑夜之神的双翼今晚把我的灵魂从这个世界带走,明天他们谁也不会想起来找我,没有人会叹息我的逝去——你们也会长久、长久地不知道你们的友人的下落!
巴黎,年,4月……
……巴黎已是今非昔比了。阴森的乌云在它一座座塔顶上疾驰,使这座曾几何时富丽堂皇的城市黯然失色。原先统治着这座京城的金碧辉煌的豪华,已用黑色的面纱罩上自己痛苦的面孔,升向天空,隐藏到乌云后面了。只剩下一束惨白的光线,它在地平线上勉强地闪烁着,如同垂死的晚霞。革命的恐怖景象把最富有的居民赶出了巴黎,最显赫的贵族远走异国他乡,留下来的人则大多生活在自己亲友的狭小圈子里。
H神甫和我一起走在圣昂诺列街上,他一边走,一边用手杖指着如今空空如也的一幢幢大楼说:“这里,原先每逢星期日,巴黎最时髦的女士,最显贵的人物和最有名的机智俏皮的人物都在д·侯爵家聚会:有人玩牌,有人则议论人情世故、缠绵的感情、种种风流快事和美好的雅趣。在这里,每逢星期日,思想深刻的男女政治家们都聚集在A·伯爵夫人家中比较马布利和让·热阿克,并构筑种种乌托邦蓝图。在那边ф·男爵夫人家,每逢星期六,M在这里朗读自己对《存在篇》一书所作的注释,向那些好奇心很重的女士们解释远古混沌世界的特征,他把它描述得如此可怕,使女听众们一个个由于惊吓而晕倒。阁下来巴黎迟了一步,幸福的时光业已消逝,愉快的晚宴已经散席,高尚的社交界都飘零四方了。д·侯爵夫人去了伦敦,A·伯爵夫人去了瑞士,ф·男爵夫人则去了罗马,要进修道院削发为尼。正派人现在都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做什么和如何度过良宵。
不过H神甫(我从日内瓦带来一封他的兄弟H伯爵给他的信)对我说,法国人早已不会像路易十四时代那样寻欢作乐了。那时,在名媛玛利安娜·德·洛尔姆、秀丝伯爵夫人、妮诺娜·兰克洛等人的家中,伏尔泰咏出了自己最初的诗篇,乌拉邱尔、圣·艾弗列蒙、萨拉森、格拉蒙、孟纳日、别利松、哥诺人人都妙语连珠,使满座添雅,领尽风骚。
我这位神甫接着说:“还有让拉,让拉想出开银行这个倒霉的主意,结果断送了巴黎人的财富和彬彬有礼的气派,把我们那些可笑的侯爵变成了生意人和放高利贷的人。在早先那些社会智囊团精彩纷呈,法兰西语言于愉快的戏语和俏皮话中显尽精致巧雅的功能,如今竟谈论起了……银行债券的价格,而那些曾聚集过社会中出类拔萃之辈的楼宇则变成了交易所。时过境迁——让拉逃到意大利——不过,真正的法兰西式的欢乐从那时起就已难得在巴黎的聚会上见到了。人们开始赌得昏天黑地。年轻的女士们晚上聚到一起是为了使对方倾家荡产,她们手中纸牌横飞,把优雅风度和娇媚之术忘得一干二净。随后兴起鹦鹉学舌者和经济学家,学院派的勾心斗角和百科全书派,双关语和催眠术,化学和戏剧,形而上学和政治。漂亮女人成了作者并找到了一种办法——为自己的情夫催眠。到头来我们竟用数学前提来谈论戏剧演出、歌剧和芭蕾,并用数字来阐释《新爱洛绮丝》的美妙。人人都在发高论,摆架子,耍滑头,把一些连拉辛和德·布瓦洛都不懂或不想懂的新奇的词汇引入法语,我真不知道,如果不是我们头顶上突然响起革命的雷鸣,我们最后由于穷极无聊会去干什么事。”
我和神甫谈到这里就分手了。
巴黎,4月……
为什么我的心有时会无缘无故地痛苦?为什么天空阳光灿烂时,我眼中的世界却会黯然无光?那突然袭来的忧伤是如此残忍,使我整个心灵揪紧和发冷,这又当怎么解释?莫非这忧伤正是遥远的将来将会有灾难临头的预感?莫非它不过是命运将会安排给我的那些苦痛的先兆?
六时许,我在愁肠百结中漫步巴黎城郊。我来到布隆森林,见到那座建于十六世纪的哥特式玛德利特城堡,它周围为一道道深沟和阴暗的拱廊所环抱,阶台上长满高高的野草。曾几何时,弗朗索瓦一世在这里尽享男欢女爱和荣华富贵之乐,在竖琴和吉他奏出的温柔之乡中流连忘返,竭尽风流。如今,这个地方只剩下一片空旷和沉寂……在我周围,鹿群奔跑;夕阳正斜,密林里风声萧飒。我想一睹城堡内的风光……台阶上有不少浮雕,是表现奥维德《变形记》中各种场景的,但都盖满了青苔。为季丝芭而殉情的彼特拉姆徒然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如今他头上飘荡着阴冷的苦蒿。另一处是尤诺宁的复仇场面,他把惹了祸的谢美列娅化为灰烬,可惜时间之手正在抹平这画面上的凹凸。在第一间、第二间和第三间大厅里,全都是空空荡荡和阴暗无光的景象。在陈设着雕刻和绘画的第四厅里,我竟听到一声沉重的叹息……我环顾四周……顿时愕然了:在这间巨大厅堂的一角,在大理石的壁炉旁,坐着一个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六十来岁的干瘦老妪,她望了我一眼,点了点头,并轻声说:
“晚安!”
我伫立原地不动有几分钟之久。后来我终于走过去并和她说起话来。这才知道她是个乞丐,在巴黎和近郊乡村行乞,她在这座空荡荡的玛德利特城堡里已经住了两年了。
我问道:“这里没人打扰你吗?”
“谁来打扰?有次看门人到这里来,看见我躺在前房的草堆里。我对他讲了我的事,我女儿的事,他哭了,并给了我三里拉。他要我住到这个大厅里来,因为这里窗户完好,风刮不进来。是个好心眼的人!”
“你有个女儿?”
“有过,有过,可现在她在那里,在玛德利特城堡的上空。唉!我和她原来就像是在天堂里:我们有一间低矮的农舍,过着平静幸福的日子。那时的世道也更好,人也都更善良。你知道我们村里人叫她什么?男人叫她夜莺,女人叫她红胸鸲。她喜欢坐在窗下或是在小林子里采花时唱歌,人人都会停下来听她唱歌。我简直高兴得心花怒放。那时候,债主不逼我们,只要露意莎求一求,谁都答应缓一缓。露意莎死了,我被赶出小农舍,只有一根拐杖和一个口袋。你去讨饭吧,去把眼泪流到冰冷的石块上。”
“你没有亲戚?”
“有。可如今都是各顾各,谁会管我?我也不愿去招人厌烦。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个安身的地方。你知道吗?这是从前弗朗索瓦皇帝住过的地方。我替代了他的位置。有时夜里我觉得,他还和大臣们、将军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和他们谈论往事哩。”
“你在这里不害怕?”
“害怕?不,我早已不会害怕了。”
“你将来怎么办,善良的老太太?等你将来病了,两腿因为上了年纪……”
“怎么办?我一死——人家把我一埋,就一了百了啦!”
我们沉默了……我走到窗前,眺望淡淡的夕阳映照下巴黎郊区的各种景象。我的上帝,在物质世界(我想)里有多少富丽堂皇,而在精神世界里又有多少贫困灾难!一个为自己的存在所累,在世态炎凉的茫茫人海中形影相吊,无人理睬的不幸的人,能够享受到你的灿烂辉煌吗,金色的太阳?还有你那纯净的澄蓝明亮的天空?还有你们的美丽景色,翠绿的草场和树林?不,她疲惫不堪,这个可怜的受苦人永远和处处都疲惫不堪!漆黑的夜,你把她掩护起来吧!喧嚣的风暴,你把她带走……带到善良人不会忧伤的地方去,带到那永恒的海洋的波涛能使如同死灰般的心灵苏醒的地方去吧!……
太阳已落下。我握了握可怜的老妪的手,回巴黎了。
巴黎,5月……
我现在在想,对巴黎,该怎么描写才最引人入胜呢?一一列举这里的宏伟艺术建筑物(它们可以说是星罗棋布于所有街道上),各种稀有的文物和华丽与雅致兼备的珍品,这自然有其价值。但与其作十个这种最最详尽的描述,我还不如简单地描述或是勾画出一些特殊人物的肖像画廊,这些人物并不住在高楼大厦,而是大多住在高高的小阁楼和拥挤的角落里的值得尊重的巴黎人,他们都默默无闻,但却值得一顾。这可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简直可以搜集到上千个有趣的故事。正是在这里,贫穷、缺乏生计逼得人什么千奇百怪的鬼主意都想得出来,耗尽了他的理性和想象力。这里有许多人每天出入游乐场和巴列罗雅丽宫,甚至去剧院,他们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抹白粉,穿黑袍,佩长剑,背着大钱袋,却没有一分钱固定的收人,可是日子过得快快活活,而且从表面上看去,像天上飞鸟那样无忧无虑。靠什么生活?办法各种各样,无穷无尽,而且除巴黎以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这些办法。譬如,有个衣着讲究的人坐在夏特莱咖啡馆喝巴西咖啡,看上去彬彬有礼,殷勤大方,不停地讲着各种趣闻轶事。你们可知道,他以何为生?卖剧院海报和五花八门的各种印刷通告,这里墙上都贴满了这类玩意儿。当巴黎夜深人静时,这个人就走街串巷去搜寻自己的饭食,他从墙上撕下各种印刷招贴,送到需要用纸包馅饼卖的人那里,并因此得到几分钱或是两个里拉,或是整整一个金币,然后他在某个阁楼里的草垫上躲下,睡得也许多克罗伊斯式富豪都香甜。还有一个人,他每天都在公众场所露面,也就是说去杜里叶里园或巴列罗雅丽宫,看他穿长衫,你会以为他是个文书,其实是个小倒贩。不过,你们猜猜,他贩什么?他倒贩的是……太太们在听意大利歌剧时丢失在剧院里的别针。他在帷幕落下,观众纷纷退场时经剧院经理许可,进到剧场,趁正熄灭烛灯时走遍所有包厢去拾拣别针,不管这些别针掉在什么地方,没有一枚能躲过他耗子般的眼睛。在仆人要熄灭最后一枝烛光的那个时刻,我们这位倒贩正好拾起那最后一枚别针。他说:“上帝保佑!明天我不会饿死了!”——然后他拿着自己的纸袋跑到一家小铺去。——我还去过玛扎林诺夫图书馆,随意浏览一排排书架上的书。一个穿黑袍的白发老人走过来对我说:
“您想看看某些有特殊意义的典籍和手稿吗?”
“当然想,先生!”
“我愿为您效劳。”
于是老人让我看一些稀有的版本和古代手稿,一面不停地讲解。我以为他是图书馆馆员,其实根本不是。他在这里充当图书爱好者和读者的活目录已经三十年了。图书馆馆务委员会的馆督允许老人在馆里做此营生,靠这个赚口饭吃。您给他一个金币也好,一个铜币也好,他都同样感谢,绝不会嫌少,不会皱眉头。即使给他一堆银币,他也不会向您鞠躬时把腰弯得比平常低。巴黎的乞丐都想要保持上等人的派头。他收取施舍并不感到羞耻,但如果以粗言相加他却要和你决斗:他身佩长剑!
在这个特殊人物的肖像画廊里,还有一个人绝不应屈居末位,他是位斯多噶派,此地人们称他为“十四头洋葱”。是个真正的第欧根尼式的人物,拒绝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他靠当搬运工为生,全部财产是一只大筐。白天他给衙门里运送各种东西,夜里却睡在城市广场上的柱廊下,就像安睡在壁龛里一样。四十年来他从未换过身上的坎肩,必要时缝上补丁,这样使它不断更新,就像医生们所说的大自然在不同季节对人体进行新陈代谢那样。他每天的食物是十四头洋葱。别以为他这样生活是贫困所迫,根本不是,穷人若向他乞讨总能有所获得。还有人向他借债——而这位巴黎的第欧根尼从不索回债款,因他每天挣三四个里拉。他能做善人和朋友,讲话不多,但言简意赅,生动深刻。许多学者都认识他。有位化学家问他:“你幸福吗,善良人?”
我们的哲人答道:“我想是的。”
“你的乐趣在哪里?”
“在工作、休息和无忧无虑。”
“还得加一项:在行善。我知道你做许多好事。”
“什么好事?”
“你乐于施舍。”
“我交出多余之物。”
“你祈祷上帝吗?”
‘我感谢上帝。”
“为什么感谢?”
“为我自己。”
“你不怕死?”
“不怕生,也不怕死。”
“你读书吗?”
“我没有时间。”
“你有时会烦闷无聊吗?”
“我从没有空闲时间。”
“你不羡慕任何人?”
“我满意我自己。”
“你是个真正的智者。”
“我是个人。”
“我愿得到你的友谊。”
“所有人都是我的朋友。”
“有恶人。”
“我不认识他们。”
第欧根尼
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没能见到这位新第欧根尼。革命一开始他就消失了。有人认为他已不在人世。他是一个佐证:积极有为、大智大慧的天才可以诞生和生活在最低微的状态中。
巴黎年6月……
我要离开你了,可爱的巴黎,满怀着感激和惋惜离开。在你千姿百态的喧闹中我过得平静而快乐,如同一个无忧无虑的宇宙公民。我怀着宁静的心情来观望你的骚动不安,如同一个安详的牧人从山上观望波涛汹涌的大海。无论是你的雅各宾党人,还是你的贵族,对我都没有任何不善之举。我听到了争论,但自己并未参加。我到你华美绝伦的殿堂里饱享了视听之福:在那里,灿烂的艺术之神闪耀着智慧和才华的光辉;在那里,荣誉的天才庄严地披戴着桂冠!我没能描绘出我的全部欢快的印象,也未能充分领受到一切,但我离开你时心灵绝不空虚:那里留下了无限情思和回忆!也许,有朝一日我会与你重逢,并将比较你的今昔变化,也许,我将会为自己精神更加成熟而高兴,或者会为丧失往日的生动情怀而叹息。倘若我能重登瓦列利昂山,并从那里鸟瞰你风景如画的郊区,该会有多么快意!我又将多么欣喜地坐在布隆森林的浓阴里重新在你面前展开历史的卷册,从中去寻找对未来的预言!可能,那时我的一切困惑都将豁然开朗;可能,那时我将更加热爱人类;或者,我将掩上历史的卷页,再也不去探究人类的命运……
别了,可爱的巴黎!别了,亲爱的B君!我与你不生于同一块土地,却怀着相同的心。我们一见之后整整三个月朝夕相处。在你的圣热尔曼旅馆里,我们共度了多少个愉快的夜晚,或是赏析你的同胞和同窗席勒的迷人幻想;或是沉醉于我们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海阔天空,议论人间万象;或是评论我们一起观赏过的新喜剧!我不会忘记我们愉快的郊外午餐,我们的夜间散步,我们骑士般的奇遇。我将永远保存你那封充满友好的柔情的信,那是你在我们分手前一小时悄悄地在我房间里写的。我爱我在巴黎的所有同胞,但惟独和你与B君的分离使我忧伤不已。令人慰藉的是,我想,我们可能会在你的或我的祖国重逢,那时可能会是另一种心境,会有另一种思想方式,但我们将彼此相知和友好如故!
而你们,我在祖国的朋友们,别因为我在异国他乡遇到一个和我心心相印的人而称我为不忠。我把这次结识视做命运对我这个孤独游子的恩赐。无论每天都有美好、聪明和有趣的见闻是多么愉快和高兴,但有一种人总是需要有和他们相似的人相伴,否则,他们内心会感到忧伤。
最后我要对你们说,除了平常有些时候会有一阵惆怅之外,我在巴黎一直过得很快乐。这样度过约四个月的时光,用一位英国医生的话说,等于是从吝啬的命运之神那里骗到一份非常丰厚的礼物。几乎所有同胞都来为我送行,还有Б君和B男爵。在上马车之前,我们相互数次拥抱。现在我们在距巴黎三十俄里处歇宿。我的心仍完全为过去这些日子所占据,因此我的想象尚未有一刻投向将来。我正在前往英国的途中,但我还没有想到它。
(本文所涉图片均来自网络)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meijiangwang.com/lxcjs/116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