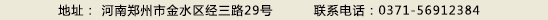远得要命的秋天
北京治疗白癜风的好医院 http://m.39.net/pf/bdfyy/bjzkbdfyy/1.地板温热得不像地板,灯管亮得像早上九点没出太阳的天空,酒难喝得真像酒。我开着电脑在放些老歌,喝了几杯酒正昏昏欲睡,听见伍佰的声音在唱“朦胧的细雨有朦胧的美”,觉得是挺美。蒙蒙细雨。通常我不喜欢他的词,土得像住在我家隔壁那位只有初中文化的大哥绞尽脑汁写出的东西。比如“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我想不出村上春树看见那句话的表情。也许笑着笑着开始皱眉,嘴唇渐渐撅起,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最后“啊,啊,挺好的”,应付过去。渡边如果写了这样的情话跟直子告白,也会被当作在认真地搞笑。然后得到“上周写的东西很有趣,虽然不像一惯的语气。是哪个漫才演员的桥段吗?”这样的回应。但我头太晕了,今晚。所以听着没那么糟。2.路上有人在锯树,“嗡嗡嗡”,一条街的树木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枝叶都变得光秃秃。街对面那家奶茶店开张三个月,生意惨淡。同一条路上已有四五家奶茶店。这家店装潢不好,为了省电费,灯光还暗得像森林里那些木屋的阁楼。于是老板想了个馊主意:重新开张。大清早开始放震耳欲聋的DJ,更把用完没扔的花篮搬了出来,包括已落灰的横幅,和一块“试营业”黑板。他相信用这种奇怪的仪式能为自己招揽顾客。我蹲在人行道上,跟一位身穿荧光绿上衣的大叔,一起看街对面的工人从云梯上用电锯“刺拉拉”地锯树,底下是奶茶店老板手持扩音器在吆喝,热闹得像过年。枝叶被锯断时,散出的气味像剁韭菜。一些直接去市场买更方便的蔬菜,如果是自己种,会很有成就感。未必好吃,但因为养活了一点东西,能开心得不行。我妈隔三差五便带回七大姑八大姨或某邻居种的蔬菜。然后你夸一句“噢,不错”,之后半个月就都要吃这种菜了。3.几个光膀子的中年人,在路边摊前站着吃炸串;一个染了绿毛的年轻人在不远处跟摩的司机讨价还价。那头绿毛,像水煮过的粽叶。黄昏的街道,总有一些小吃摊。烤鸟蛋摊位绑上了五颜六色的灯带,正亮着光。路上有大妈大婶在聊天;刚放学的小孩熙熙攘攘,相互簇拥着跑过长街。在银行门口坐着发呆时,一个穿着廉价亮片裙的小姑娘被父母牵着,正一蹦一跳、不老实地走路。那些亮片是银白色,在光线反射下变成了金红色,像南方下午六点半的太阳,仿佛披了一身云彩。我卡里余额2.7元,只够买一罐铝罐可乐。因身上的牛仔裤足够破旧,所以坐在被无数人踩过的台阶上也无所谓更脏。风吹来,地上的落叶被扬起,我转过头,看见一辆香槟银色的轿车。车头比一般汽车长,车身干净得发亮,像贵妇的手提包上反光的拉锁。那不是我见过最漂亮、或最贵的车,却是一眼认为“汽车广告里的车应该是这样”的。天边不知何时已消失的太阳,余光映出一片明朗的天空,突然觉得生命美好得让人难过。“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夏天了。”我想。如果这是一部电影,在此时结束,大约算happyending。4.老板似乎是人造人。他坐在离我大约一米的地方低头玩手机,开着扩音,店内只有我们两人。我转头看向他,说了五遍“老板,煮碗馄饨”,声音像皮球,从这面墙弹向那面墙,那面墙又弹向另一边,四面墙都回荡着我的声音。他却仍对着屏幕傻乐,全无反应。虽然不总如此。通常他喜欢跟人聊天,打听各种事。比如谁是A城人,谁最近在考试,谁跟老婆住在第二条街一间不大的房子里。上次他说:“你好像爱边看书边思考,应该是个文化人。”我确实常看书,在店里。因为没有WIFI,不能看视频,我的耳机又坏了,有WIFI也不想看。多数人会选择外放,在沙县,店内坐着的总是男人,男人之间没那么多讲究。女人在场时才顾忌这那。但我没这习惯,所以只能看书。也没思考很深邃的事,一般在想“吃完了绿豆还要点馄饨?馄饨是热的,绿豆是冷的,也许对胃不好”。或“这家伙写的什么?结尾怎么是这样?我漏看了哪儿?”后来不看乔伊斯了,便没了这样的困惑。以及越来越穷,能点的只剩绿豆汤,也就不担心冷热交替,肠胃难受了。5.傍晚我走在街上,漫无目的,不知想吹风还是想看看来往的行人。夏天总这样,闷热、倒霉、叫人沮丧,有一瞬间我以为我的朋友都死光了,否则我不会这么孤独。因为低血糖和睡眠不足,心脏供血似乎也不够活跃,电流般的麻痹感从我左胸传遍全身,走在路上,感觉一切都变得不真实。甚至对面那家旅店原本的外墙是否为褐色,都使我怀疑。我想起一片长在海边的树。经年累月的风总往同个方向吹,那些树的枝叶也被吹得往一个方向长,像抹了发蜡、梳了个大背头的人,远远看去还以为是大型蒲公英。我在那片树林中见过日出,却没见到日落。途经那里时,我想跟他们说:“别去坐船了,留在这吹风吧。那小岛都是些虚假的树屋,我都能看见钢结构。在那样的地方没什么好玩,不如在这等黄昏到来。”但我不想扫兴。那天他们兴致勃勃,觉得在人工岛上玩些游客喜闻乐见的娱乐设施会很有趣。不能因为我发神经,就希望别人也陪我一起看日落,从早上八点。6.我有两幅耳机,一副森海塞尔,一副威索尼克。森海坏了有段时间,威索尼克是在我还没一贫如洗前买来当替补队员的。后因佩戴体验极差,音色也差点意思,所以气得扔在床头柜,落灰了半年。大约两个月前,森海报废,手机上的音乐应用再没打开过。因此,少了出门散步的一大动力。我不喜欢人们大声交流的声音,和闲得无聊瞎按喇叭的车辆,没有耳机的生活于我而言是一种煎熬。赶巧的是威索尼克也故障了,接触不良或线材问题,如何调整接口都有一边哑火。但有时你就是突然想听首歌。凌晨三点,抱着一点微渺的期望和“不行算了”的怨气,以一个别扭的姿势,耐心调整几分钟后,它竟恢复正常了。于是我躺着,循环了七八遍《LightningCrashes》和《TaMain》。风扇在床脚朝我吹着风,顺便把耗电速度和直接往火里扔纸钞差不多的空调打开了。我仿佛坐在一辆开往未知前路的皮卡车的后车厢,夜空浩瀚,星光如萤火坠落。月色温柔,如行驶在静谧的湖面。天地间万籁俱寂。这没能与我好好相处便已寿终正寝的耳机,仍把最后一点温柔留给了我。也算好聚好散。7.凌晨三点,牙疼得睡不着,捎带着头也疼。想起苏格兰人的鬼话,他们说:“当你感冒时,喝点威士忌;当你牙疼时,喝点威士忌;当你被女人甩了,喝点威士忌。”威士忌好像包治百病。我因此喝了半杯。牙疼稍有缓解,头却疼得更厉害了。“卡尔里拉”是一家地处艾雷岛的威士忌酒厂,这个岛上出产的威士忌大多有一股消毒水或皮革气味,但并不很讨人厌,尽管第一印象往往不好。如果适应了这种味道,会觉得还挺浪漫。仿佛躺在临海的小山坡的草地上,毛毛细雨轻飘飘地落。远处灰蒙蒙的天,和海面终年不散的雾,让人想到所有结局并不美好的爱情。这瓶酒我开了两年,酒液所剩无几,味道也散得差不多了。尽管如此,仍叫人喜欢。只是没料到最后一杯是因牙疼而喝。真是个严肃的理由。8.“Asparagus”这个词,既是龙须菜,也是芦笋。毛姆在某短篇小说中提到,说它价格昂贵,但口感极佳,一咬一汪水。我问朋友吃没吃过龙须菜,她说涮火锅时常吃。我觉得不对,如果是涮火锅时吃的菜,尤其如她所说“挺便宜”,那毛姆不至于在请客时因对方点了这道菜而心疼钱。后来看的另一个翻译,说他们吃的芦笋。我没想通,芦笋是烹饪后仍鲜美多汁的菜?“多汁”怎么能形容芦笋。但毛姆都挂了,我也不能左手龙须菜右手芦笋,问他“你点的是这道穷人也吃得起的火锅菜,还是口感如树枝的芦笋?”他要回答“都不是,是更罕见的”,我就只能左右开弓往他脸上甩了。他该形容下具体长什么模样,如“像竹竿”,或“菜叶丰茂”,而不是用个易引起歧义的词。搞得我大半夜在脑海里想一道虚无的菜,却不知盘中摆的是什么。不过文中提到“融化的黄油”,芦笋的可能性就更大。我不止一次看见人们往烹熟的芦笋上淋黄油。虽然芦笋之类外形千奇百怪的菜我从不喜欢,像近几年大热的秋葵,说什么营养丰富,可吃起来粘了吧唧,还难入味。结果吃最多还是青菜和白菜。奶白菜尤其好,兼具两者的优点。既有白菜的爽脆,也有菜心那种仿佛咬了一把青草的口感,简直完美。9.一些黄色干枯的落叶,被阳光晒得失去了水分,身子蜷成半圆。风吹来,一片片在地面滚动,看不真切,以为是身躯小巧的田鼠,在逃窜躲避来往的行人。走到南巷时,一辆高大的巴士在车前窗挂了一圈五颜六色的流苏,像庆祝什么节日。司机把车停在路边,靠在驾驶位上,伸直了双腿,双手放在脑后枕着。十分惬意。虽然叫“巷”,却是左右连通的马路,宽度可供两车并行。不是会让人在脑海中浮现出青砖与高墙的老街里的巷弄。那辆车载了一帮背着非洲鼓的小孩,大约是兴趣班。他们走到附近一片空地,“咚咚咚”地乱敲起来。为首的女人,三十五六岁模样,叫他们停下,开始示范正确的节奏和敲打的手势,说了些“大鱼际”、“小鱼际”、“指肚”之类的名词。那帮小鬼一边点头,一边继续乱敲,沸反盈天。道路两旁的树,因绿化工程被锯得光秃秃。像发生过大火。叫木头还更贴切。但秃子也是人,人不会因没了头发就变成鸡蛋,树当然也不该被严苛地要求。于是他们继续“咚咚咚”,风继续吹,地上的田鼠继续跑。我站在大巴车旁,看着眼前的热闹景象,料想今年将有一场大丰收,足以让人们在果子未熟前便开始载歌载舞的丰年。秋天也许不远了。10.小区门口常见一类面包车。泛黄的白色车身,不少剐蹭痕迹,车窗内永远卡着一块写明业务范围的长方形泡沫板,“修补天花板及地砖”几个大字格外显眼。几乎所有小县城都有一辆这样的面包车,一辆车便是一户人家,移动的房子。吃、住、行,都倚仗于此,大约算中国的吉普赛人。下雨天,那车的男主人会打开窗,仿佛天上落下了钱币,抬头看看云,又期待地望着远处,笑盈盈地点一根烟,哼起小曲。雨后他总能等来生意,倘若当天雨水足,也许不止一笔。来的人会先询价,然后讲价,最后不得不同意他的一口价。他心里清楚,会在雨后赶来问价的,早已忍受漏水的痛苦许久,这对他而言是好事。这算狡猾么?当然不算。车上住着他的妻儿,还有一口大黑锅,用来熬那些黑色沥青或什么胶质的难闻的铁锅。一个住在面包车里的人,如何对有片瓦遮身的人心生同情?他连片瓦都没有。但他不会在原地待很久。一个小区里漏水的人家有限,雨季也有结束的时候。一连四五天都没雨,他便会上路,去往下一个城市。老婆和孩子熟练地将车门外放置的生活用具收回车内,车厢顶部的喇叭被打开,伴随“修补天花板,渗水地砖”的声音响起,引擎发动,抖落下车身的灰,吉普赛人又上路了。11.跟喜欢匡威的家伙看老电影真是世上最无聊的事。上一秒你们还在讨论剧情,史泰龙伤心得要死,打了几年拳没有专业教练帮忙,下一秒他们就在惊呼:“噢!匡威!他穿的是匡威!匡威真是恒久的经典!”是吗?他还吃了鸡蛋,你知道鸡蛋?鸡蛋是你家祖宗还在黄河流域附近捕鱼时就已经出现的食物,你怎么没感慨一下:“鸡蛋!他吃了鸡蛋!没想到洛奇也吃鸡蛋!和我在楼下超市打折后买的6毛钱一个的鸡蛋相差无几!”12.在我的童年时期,我们家有过一辆车,空间不大的小轿车。所有那个年代的中年人、有车一族,都会在副驾驶前头的平台上放一罐柠檬或花香味车载香水。第一次闻到那东西时,我嚷嚷着要吃一点,因为是膏状,颜色还挺好看。当然,我没能拧开盖子。后来,也许有一样喜欢那香水的家伙,发现了把廉价茉莉花茶和柠檬混合,会得出差不多的味道,连喝起来都一股人工味。我在公交站牌前杵着,一边喝那杯恶心的饮料一边看风吹塑料袋。天空阴沉沉,风刮个不停,透明塑料袋被吹来吹去,随着风向打转。我想,“应该有个穷丈夫,下班后站在这抽了几根烟,然后努力挤出笑容,若无其事般走回家了。”因为站牌下掉落一地的烟头,是七块钱以内的。也可能是一个等了太久车还没来的穷小伙,他要去赴一场约会。约会前还抽烟?当然。这是一个人均收入极低的城市,人们约会的地点甚至能选在只花16块钱就可坐一下午的奶茶店,抽几根烟不奇怪。那姑娘说不定还会把拖鞋一踢,露出没刮干净腿毛的大白腿,跟男人们聚在一块打牌。13.我住的城市有海,见的次数不多,却并不稀奇。有些北方的人,想去南方生活,他们以为那里冬暖夏凉,一切美好。但南方有南方的烦恼,有湿气,有阴雨,还有台风。可能唯一相同的,是无论南北,都有叫人失望的人生,都有避不开的彷徨与孤独,失落与惆怅。14.半个月前,A跟我讲了个关于酒店和矿泉水的笑话,什么他老妈喝了酒店里的矿泉水,然后出门买回一瓶放归原处,省了18块钱。一星期前,B跟我讲了一遍。三天前,C又讲一遍。直到今早,我还听到这个笑话。我说我听过三遍了,对方难以置信,“怎么可能?我才听说。”“第一个跟你讲这笑话的是谁?”“苏格拉底吧。”我说,“那会儿他跟老婆吵架,被赶了出来。”“哪个‘苏格拉底’?”“希腊那个。”“胡扯,那得有几千年了。”“对,你知道他为什么跟他老婆吵架?”“为什么?”“因为他讲了一个在山洞里看见的,原始人刻在石壁上的故事。”“什么故事?”“关于谁的老妈在酒店里喝了一瓶矿泉水的鸟故事。”“……”15.巷子里有家理发店,老板娘五六十岁。我的头发总是在那剪。“我剪了三十多年头发了,从望海路的小店铺,后来骑着一辆三轮车,把所有东西搬来这,三十多年。”她说。我信任她这些年积累的经验,且不喜欢年轻人在我头上揉弄来去,毕竟不需要一个新潮的发型。从不被家里要求必须剪寸头起,我的发型就再没变过。三十多年做同一件事,这种坚持已不全是为了谋生。我也在别的店剪过头发,结果留长后被她一眼识破,“谁把你头发剪成这样?怎么能这么剪。”我说一个年轻人。她说怪不得,年轻人就是毛手毛脚。“甚至鬓角都没给我刮。”我说。“鬓角都不刮?这得懒成什么样。”然后又自言自语般说了一串“阿姨剪头发多年了,还有从外地回来就找我的,可不单是因为我剪头发便宜”。有时赶上店内人多,走到门口刚准备折返,她从镜子里看见,便叫住我,让我先去转悠一会儿,或下午再来。结果下午睡过了头,晚上八点半才到店,她责备道:“说好下午来,却拖到这时候。”这话温暖得让人以为世上仍有人在时时惦念你。只要还有人等你,你与这座城便是有联系的。哪天离开了,也会留下一根线,深深浅浅,伏在回忆里。何时想再循着轨迹走回来,也不会太费劲。16.因睡不着,喝了几杯酒。酒精的麻醉作用总生效缓慢,但约莫两杯下肚,便使人食欲大增。如今又是夏天,天气闷热就想吃秋刀鱼,尽管我不擅长吐刺。配稀饭与咸蛋,倒是极好。大学时,我们常在夏天吃烧烤。凌晨两点,路边的烧烤摊老板光着膀子,用蒲扇扇火,时不时以手背揩去额头的汗珠。秋刀鱼端来,炙烤后滴落盘中的油花仍腾腾冒着热气,洒上些细盐,鱼皮焦香,肉质嫩滑。但那时我不爱吃这种鱼,刺多是一方面,难入味也是个问题。秋刀鱼是很磨人精神的食物。古时候的士大夫大约会以此为修行。正襟危坐,屏气凝神,一筷子仅夹起指甲盖大小,不够尝出半点味道,却偏不放开拘束。所谓“君子”,不就是既能约束德行,也能约束吃相的人?所以我不是君子。如果没人盯着,别说筷子,没直接提起鱼尾,刨木机般吃得遍地狼藉才怪。不仅如此,还要吧唧嘴,“嘎滋嘎滋”,嚼口香糖似的将声音播散开,把所有一听见食物被嚼碎发出的声音就狂躁的人气到脑中风。想到这就开心。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秋刀鱼似乎总一脸“难以置信,我竟然死了”的蠢样。鱼嘴微张,眼珠瞪得老大,直挺挺地板着身子。仿佛不相信青春消逝得如此之快的我们。17.偶尔想回乡下种地,外公给我留了一小块地,听说是种菜的好土。我妈始终认为农村是废物待的地方,也是无用的人才种地。可我想,“我不就是废物?因此想回乡也不难理解。”农村唯一难适应的,大约是水。即便煮熟了仍有一股奇异的涩感,像吃下太多炸面皮,嘴唇内侧生出青苔般的糙。也是因水,和老一辈人爱用铁制的碗碟盛放食物,使得一切熟食都有股怪味,在鸡鸭肉上尤其明显。这种情况下,只好吃些简单的蔬菜,如红薯叶,佐以虾酱炒,是一绝味。在穷苦的地方吃穷苦的菜是理所当然。至于虾酱,虽叫“虾”,其实虾皮都不算,用放大镜才能隐约分辨出内容。黏糊糊,不美观,却异常鲜美。我们村离集市二十分钟车程,这个时间是以一辆最老的摩托车算的,地处不算偏远。只是天晓得为什么,至今仍是黄土路,十年前能踩到的牛粪,十年后还在。连那头正嚼着一大把嫩草的水牛,好像也是十年前的。不同的只有我们住的那条巷子,多了个简易的路灯,没有支柱,只有头,飞刀般斜插在高墙上。村里的老人有些死了,有些愈加辛苦地活着。这使我意识到,有些东西不是时间没法带走,只是被暂时饶恕了,如村里的路,路上的牛,牛脚下的粪。但它将来时,谁都躲不过。18.《在路上》一直没看完。里头提到的地名太多,还都是真实存在的,这给阅读造成了一点阻碍。我要去思考俄亥俄州在哪,衣阿华在哪,内布拉斯加又在哪儿,偏偏不想看地图。使生活便捷的东西很多,但便捷往往意味着失去一些体验。于是书中主角停在了普拉特,刚刚有人去小便。什么时候我想继续读了,他那泡撒了几个月还没完的尿,才能终于提上裤子。19.路边有卖衣服的摊位。一些廉价T恤被挂、或堆叠在一个巨大的塑料盆里,旁边立着“十元一件”的牌子,卖的多是年轻人不愿穿的款式。老土的配色和图案,还带亮片。一帮大妈大婶围成一圈在挑挑拣拣,很是热闹。当中有一位,深棕色短卷发、身材矮胖、右眼瞳孔泛白、也在选着衣服的,是曾经一家饭摊的老板娘。那时她有一辆巨大的推车,一个成年男人那么高,长度也差不多躺下一个人。推车上三面玻璃,围成半堵透明的墙,当中放着刚炒好的热菜,底下是塑料袋和一次性餐具。卖的菜不贵,素菜五六元一份,带盒米饭,荤菜九块钱可以打一盒五花肉。她那摊位几乎是这一带最受欢迎的。后因环境整治,被勒令不许再出摊。三年前某个中午,我一如往常去那打包饭菜,前边乌压压挤了很多人,我便在后边站着,等人群散去。谁知散了一群,又来一群,也没人排队,全都站前边嚷嚷要打包这个打包那个。她见状,伸出手、往旁边一推,把那几人全揽向一侧,指着我说:“他先来的。”人群顿时静了下来。我被众人注视着,仿佛开设了专属通道,点好餐,慢悠悠地走了。这件事我一直记着。甚至把她列进了“如果中彩票有了一大笔钱,应该给他们一份,使生活好转”的名单。她排得挺靠前。20.如果你的连衣裙洗褪色,或积了层皱纹般掸不去的灰,可以跟别人说那是“波西米亚风格”。谁都不知道波西米亚是什么风格,但一切都可以往上推。你家热水器坏了、空调失修、男友劈腿、学业不顺,都是波西米亚风格,你活在波西米亚的人生里。21.蚂蚁这种既无耻,又有家庭观念的生物。无论你把房间打扫多干净,都一定会在隔段时间后从地板或什么角落里发现它们的身影。一开始是一只,用卫生纸一捻,连同地上的灰尘和脱落的头发扔进垃圾桶。第二天它爸妈就找上门,两只蚂蚁在房间里闲逛,看见你还若无其事地问“约翰呢?昨天约翰来你家串门”。顺手把它爸妈带走,及地上脱落的头发。第三天,祖父祖母七大姑八大姨远房表舅都来了,“约翰呢?约翰前天来你家串门。还有菲利普和艾米丽。”它们嚷嚷来去,咿咿呀呀,桌底下几个混账已经在翻你的垃圾桶,找些隔夜剩饭剩菜和食物残渣。第四天,几乎举族搬迁,你还没睡醒就感觉腿上痒痒的,不知是风吹动了腿毛还是静电,睡眼惺忪地定睛一看,“你把约翰、菲利普、艾米丽、科尔、乔纳森、弗里德、克莱尔、叶琳娜……怎么了?”干。而且它们并不从事生产,只是到处收集东西,进别人家也不敲门,把穷人的饭菜爬满还心无愧疚,一帮鸟人。22.人行道上,用来划分电动车停放区域的低矮的铁杆,我在那呆坐了半天。不知是饿的还是渴的,也许两者皆有,我心情低落,万分沮丧。?去年朋友给我寄来一罐秋梨膏。其时我感冒未愈,颈椎难受,头、牙齿,该疼不该疼的都来了。且一如往常的穷。几乎所有认识我的家伙都对此印象深刻,“人怎么能这么穷?”好像在说水牛怎么会游泳,那种理所当然,偏偏想不通的事。??秋梨膏寄来时,我的感冒已好转。?说明书上写着“开盖后冷藏”,但南方的冬天并不能做到仅凭环境温度冷藏食物。所以我想,也许明年有钱买冰箱,说不准时来运转。于是把那罐东西一直留着。直到昨天。?我饿得厉害,一整天没吃东西;加上这段时间缺少糖分摄取,因而嘴里总是苦且干涩,心情都糟糕了许多。?之前有朋友给我寄来面包。我讨厌面包,即使是夹心的,只能做到尽可能不厌恶。我抱怨着“这东西还不如方便面”,可是方便面又不如米饭,“自热米饭如果也降到方便面一个价位多好。”“但打盒米饭顶多两块钱。”她说。?“是啊,可纯素的盒饭都得七块钱。”我说。?“你还想着吃菜啊!?”“否则呢?方便面还有几粒脱水葱花。”这让我想起初高中的一堂语文课。老师让我们在纸上写下“生命所需的五样东西”,然后依次删减,只剩最后一样。?任何一种生物,想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都不复杂,但你想长寿、快乐,就需要一堆无用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昨天我把那罐本该在下一次感冒时吃的、一次只建议服用15g的秋梨膏,一次性吃了半斤。它只有半斤。我需要一点糖分,何况我饿得要命。那秋梨膏口感粘稠,带着些细微如沙的颗粒,可能是梨子身上的鸡皮肤,甜腻得像加了半袋糖,虽然配料表上没这么说。?“这罐东西主要由梨子、枣子,及各种中药材和一丁点微不足道的甜味源制成。”“那你们有加很多糖?”“没有,一点点。”“具体是多少?”“谁知道?朋友。就像北极光,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帝打开了熔岩灯。”天空将变得昏暗了,太阳开始消失,在一层层厚实如棉花糖的云后。它准备悄无声息地离开,像某天中午趁着老爸熟睡时蹑手蹑脚打开门溜去网吧的我。?附近那家饭馆该开门了。我在之前的日记里有提到,把桌子和凳子摆在巷子内的饭馆。我在那思考过《瓦尔登湖》和一个蹬儿童自行车的屁孩之间的联系。我想去那吃点什么,如果我还能掏出七块钱。?七块钱可以打半份青菜和半份韭黄,韭黄是素菜里最值得穷人品尝的。倒不是因为多好吃,而是韭黄总要炒蛋,然后你就能赌一把运气,看看打菜大婶会不会给你来一小块煎蛋。如果有,你就算得了半道荤菜。或三分之一道。??若不是很有把握,可以晚点去,用餐高峰结束后,你走进去仍看见韭黄炒蛋,会使你的运气比原本好一些。?因为不想后边的客人看见菜盘里只剩一些被挑拣后剩余的残渣,几乎所有店家都习惯给先来的客人少少的菜,把更好的留在后头,避免卖不完。但也不要去太晚,否则什么都没了,汤也没了。?说到汤,这儿的店铺是干饭才配汤,稀饭不配汤。汤也不是多金贵,不过葱花加点盐。但干饭比稀饭顶饱,再顺便喝口热汤,感觉会没那么糟。虽然寒酸点,总归是贫穷的生活智慧。而且你可以叫店家给你的米饭淋点酱汁,卤猪蹄那大锅里咕嘟咕嘟冒泡的卤汁。?这么一来你便花七块钱买到了半份青菜、半份韭黄炒蛋、一碗带着些丝丝缥缈的猪蹄味的干饭,和一小碗热汤。??但我没有七块钱。我翻了翻破旧的钱包,和那张已蹭掉漆的银行卡,什么也没有。为避免饿晕在街头,难看又麻烦人,我只得拖着沉重迟缓的步伐,及蹲坐太久后突然站起身发麻的双腿,每走一步都像给膀胱来了次电疗,慢慢回到我糟糕的出租屋。?这房间也不知谁设计的,夏暖冬凉。夏天室内温度和湿度比室外高,冬天像在南极砌起冰屋,还不断滴水。也许半个世纪前,这里收押过所有道德上罪大恶极,偏偏没干出什么实质性伤害他人的罪行的人。?比如下雪天在消防栓上堆雪人的;将曲奇棒捅进别人家钥匙孔掰断的;买水果时把底下的好果子都挑走了的;凭借人畜无害的脸请求插队,结果一转头把她男友也喊来了的。??我躺在地上,脑海里回想往昔一切,刚搬来此地的模样。曾经干净的写字台,没发现蟑螂、也没被堵住下水管的厨房;水龙头没坏掉的浴室,光洁的地板。自从地板成为了我的床,便少了打理席子的烦恼。之前隔三差五要把竹席拿到门外抖一抖,将细缝中的毛发和身上脱落的角质抖出来,及恼人的、被静电吸附的灰尘。如果你太懒、任由它们积攒,总有一天闲得无聊,用手指弹了弹身下的席子,会发现灰尘像跳蚤一样漫天跃起。?睡地上的烦恼,只有不知何处出现的蚂蚁,和该死的蟑螂。我还想起《查理与巧克力工厂》,那部电影。他们穷得叮当响,依靠甘蓝菜度日,却有不离弃的家人,和一幢摇摇欲坠的房子,几乎被风一吹就掀掉几片瓦。四个老人同睡在一张床上。即便穷困潦倒,母亲仍把家努力操持好,甚至想出了“往汤里多兑点水”,这种无可奈何的办法。避免被察觉家中的困境,顺便多撑些时日。那锅汤被炖得像浮着几片碎叶的洗菜盆。
上一篇文章: 东方市急销农副产品爱心认购倡议书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转载请注明:http://www.meijiangwang.com/lxczf/107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