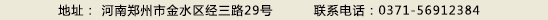陈文茜蒋勋不敢尝试另一种生活改变无
文
文茜的异想世界
图
网络
文茜观点我们很多人崇尚池上(池上乡,位于台湾台东县北部)的风景,脑海中常常浮起要去池上的念头。而有一个人将这个念头付诸于行动,并愿意在那里长久地待下去。
他是诗人,也是画家;他拥有音乐般好听的嗓音,他是蒋勋。
1◇陈文茜:蒋老师,好久不见。
◆蒋勋:真的好久不见了。
◇陈文茜:你去了哪里?
◆蒋勋: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池上。画展前把画都交出去了,感觉筋疲力尽。我跟朋友说,画画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每天跟画布在一起像谈恋爱一样。但是办画展就像办婚礼,我觉得办婚礼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一生没有看过让我觉得很棒的婚礼,因为大家都疲于奔命。所以我4月又回巴黎住了一个月,回来就是画展开幕的时候。现在都结束了,所以感觉人会比较放松。
◇陈文茜:你办画展的时候我也有收到邀请,不过那时候我在美国,我听说非常多人去看。蒋老师,你在池上住了多久?
◆蒋勋:一年多,到现在将近两年。
◇陈文茜:池上和巴黎可以看做是两部分的你,在池上呆了这么久去巴黎,再在巴黎呆了一个月回到池上,你觉得两地的区别是什么?
◆蒋勋:我现在觉得,我们过去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他在台北事业做得很大,但是很不快乐。每当焦虑烦躁,他就会说,「我不要做了,反正我这辈子钱已经够花了,我要到台东去养猪。」刚开始我会被他这句话感动,可是他讲了20年,也没有真的去养猪,我就觉得,这真的只是他的一个梦想。
我常跟朋友说,其实在台湾,你去任何地方就是三四个小时的事,没有那么悲壮,也不用破釜沉舟。我去池上以后,可以很笃定地说,我变得更爱台北,也更爱巴黎,因为它们是那么不一样。在池上,我可以没有电视和报纸,就只是画画。每天我都能呼吸最好的空气,吃「保庇素食」的野菜。我会想念台北的牛排,想回台北听曾宇谦(小提琴演奏家,被誉为「台湾之光」),看PinaBausch(德国现代舞舞蹈家),这样两种生活,真的不必把一边切断到另一边去。
◇陈文茜:其实这就是很多人生活的两个部分,没有必要为了A否定B,或是为了B去否定A。
◆蒋勋:有可能过去我们真的是误解了。很多人不敢尝试另一种生活,是因为他们觉得改变需要破釜沉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在《池上日记》里讲到一个年轻人叫罗正杰,他是新竹人,在台北做设计做得很成功,但是他很忙很焦虑,身体也不好。后来他开始环岛,然后爱上池上。他一直在想生命的这两种状态要怎么平衡。后来他在中山路99号看到一个老诊所,荒废了好久没有人要租,他问了房东租金是一个月一万台币,就签了9年的约,把房子做一下整修。现在他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台北见客户,剩余的时间就呆在池上。他说,很多东西通过实时视频对话,全都可以完成。他现在30岁,非常快乐,生活很平衡。最近看到我,他说:「我最近回台北,变得特别爱台北。」我觉得这是对的。
我现在回台北,坐在地铁里,会觉得很好看,有戴着耳机的人、疲倦的人、看手机的人......这些在池上都看不到。我这次画展,有两张是画台北地铁里的人。过去我会误解,认为生活需要二选一,其实这样的人生常常是错误的,就像公投一样,太可怕了。要知道很多东西是很多重的,你必须考量到很多可能性。最近两年我觉得太开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的人生可进可退。
◇陈文茜:没错。然后蒋老师还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一般人到台东,要快一点就坐飞机,或者坐花东纵谷的火车。蒋老师从台东走南回铁路回来是三小时,走花东也是三小时,你就像蒋公在巡视国土一样,一会儿往这边走,一会儿往那边走。这样讲对吗?
◆蒋勋:哈哈哈是的。我昨天回来是坐南回铁路,三个半小时左右,大武(台湾台东县东南方)那一带的海非常美,我拍了照马上传给朋友,他们以为我又去希腊。到了高雄就可以坐高铁到台北,才一个半小时。如果从台北下去,可以走纵谷。具体要看季节,不同季节我会走不同的路。如果是春天,我会走纵谷,沿途的苦楝漂亮极了,那里有很多老的苦楝树。
◇陈文茜:对,那种紫色的花很美。
◆蒋勋:沿路都是风景,真的很快乐。其实人生很短,从生到死,从A点到B点,就像是火车从起点到终点,但是如果你认为每一站都很有意思,那就会变得不一样。我昨天回来,中间都不停站,我从谷庄下车,那是一个很小的原住民的部落,我从来没去过,就会想要了解。
◇陈文茜:这么长一段时间没见,你皮肤变黑黑的,看起来好像希腊人。你自己觉得呢?
◆蒋勋:哈哈哈,呆在池上不可能不变黑。我觉得在池上真的很开心。最早柯文昌创立台湾好基金会,他说了一句话:「台湾的好要从乡镇做起」。我很感动,可是后来我觉得这还是偏理论,一定要真的住在那里才会知道。我住在台北没有办法想象,真的去了以后住在一个老旧的国中宿舍里面,很像我小时候公务员爸爸的家。我早上起来打开门,看到门口一堆木瓜、丝瓜。我吓一跳,到处去问是谁给我的。我想你明白的,你如果住在帝堡(台北顶级豪宅),一打开门发现有很多地瓜、丝瓜肯定要吓坏了。到黄昏的时候,有当地人过来说:「你们台北人真的很奇怪,我们的木瓜树一结就是四五十个果子,反正吃不完,当然就会分在各家门口」。
◇陈文茜:所以你不是唯一收到的人。
◆蒋勋:对,现在我打开门看到这些,我就不管了,直接拿来吃,有很多龙葵、龙须菜这些。有一种理论叫「土地伦理」,就是要分享。像梁振贤平时非常善良,但是这个季节因为要抢收,他真的是六亲不认,因为如果一阵雨下来,稻穗全都泡烂了,今年就完了。所以他们抢收的时候,就看到几家人帮着一家人一起做。我忽然觉得很快乐,是那种分享丰收的快乐。一万公斤的稻谷称重居然能得到一万三千公斤的米,说明它的质量达到最好。当地人一直到土地庙去拜拜,我说那如果欠收呢,他们说那也一样要拜。他们跟我说池上是土地庙最多的地方,他们会「敬天敬地」,而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得到我会觉得是应该的,得不到就怨天尤人。像梁振贤这种半世纪脚都在土里的人,现在变成我的老师。
◇陈文茜:梁大哥他们让池上变得很不一样。
◆蒋勋:对,他不会惊慌、不会闹情绪、不会怨天尤人。
◇陈文茜:梁大哥来我的节目,很害羞,三分钟讲不出五句话,害我很慌张。但是后来我想应该要跟他学习「慢」这件事。蒋老师,我听柯文昌说,你现在每天下午都去喝四神汤和杏仁茶。
◆蒋勋:对,当地传到第三代的赖平宇会做一个四神汤,一定要三点钟去,十一点没有熬透,三点以后就没有了。我画画到三点,就自然会有一个东西让我停掉,赶紧去喝四神汤,到黄昏的时候再喝杏仁茶。我曾经问他,这么多人来喝四神汤,为什么你卖完不做第二锅?他就笑笑看看我,觉得那不是他想要的人生。那是我在学习的东西。
◇陈文茜:你会不会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东西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会觉得那些没有发展性、太沉闷,自然就离开了那个圈子。
◆蒋勋:我们离开了自然秩序和土地伦理。在都市里,人感到不快乐、焦虑,最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你不知道下一个焦虑到随机杀人的人会不会就在你身边。其实郑捷(年台北南线列车随机杀人案凶手)枪决的时候,我在池上为他念了一遍金刚经,因为我觉得很痛心,他其实也是受害者。我们其实一直忽略了,在城市里,生命密集到一个程度之后,人会焦虑到不行。有一阵子我在地铁里,我也感觉很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挤成这样,为什么不能优雅一点,好像那个空间逼着你没有办法去爱别人。可是在池上这个全台湾医疗设备最差的地方,90岁以上人口比例是最高的。当地卫生所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要不要去宣扬这件事,这样说好像在反医疗。
◇陈文茜:我突然觉得你会活到90岁。
◆蒋勋:那里就是空气好、水好、土好。梁振贤阿嬷(闽南语中表示祖母或外祖母)去世的时候岁,挂着红灯笼像办喜事一样,最棒的是她生前从来不用吃药打针,就是穿着拖鞋满街走。我就在想,我应该找回什么?或许医药也应该适可而止了。
◇陈文茜:我每次出国都会买伴手礼,我会在台湾好基金会买池上的米,所有人看到我都问我有没有带米来,没有人跟我客气。
◆蒋勋:我4月去巴黎,带了池上的米两包、玉蟾园的豆腐乳两瓶、南门市场的酒糟和酸白菜。我进关的时候在想他们可能会查,结果早上6点钟到,他们一面打哈欠一面盖章,我就知道肯定没问题。
2◇陈文茜:蒋老师最近出了《迟上印象》,是你的画册,还有新书《池上日记》。请您念一段《池上日记》里的文字。
◆蒋勋:「下雨了,春天的纵谷总是无预警下起雨来。槟榔树站在雨中,像一排一排整齐的队伍,还有山坡上一个接一个累累的坟冢,还有水田里刚刚修好、一列一列的秧苗。我的车窗玻璃上有一滴一滴滑下来的雨珠,鹭鸶依次飞起、降落,明亮洁净的白像陆续落下的雪片。但是这里是不会下雪的南方,所以纵谷的记忆像长长的铁轨,不断在身后消失。从部落失去的山林猎场到关山光绪年间的天后宫,从百年的老茄苳树到日本修建的玉里神社,从客家移民院落腌制的老菜脯到河南老兵喃喃自语的乡音,我在薯莨染色的苎麻布前细看手工织纹,来来往往、纵横交错,像是古老故事脉络的经纬,线索依然清晰,却因为阳光旧晒,已经褪色,早已失去可以解读的语法。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失去的母亲的语言都将是我此后反复吟唱的诗歌,你是否在意,最深的心事总是不可解读。」
◇陈文茜:刚才你讲到,从池上回到台北会觉得很好玩,看到玩手机的人、烦躁的人、疲惫的人......这些在池上都看不到。我在《池上印象》画册里看到一幅画,画的是旭日,你在旁边写了一段文字,说你不敢眨眼,就怕错过瞬息梦幻般的光。你提到在池上,随着季节的变化,春分以后,纵谷的旭日就会明显提早,你喜欢在田野里看旭日曙光的变化。其实我们平常在城市里也可以看到日出日落、看到月亮,但是很久都不会抬头看一眼,我们总是错过,好像只有到了大自然里,不再有距离的地方,你才会想起去看这一切。
◆蒋勋:在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科技不断发展,像用电,现在已经很难自觉节制。我童年的时候,其实没有用到这么多电,也对电很珍惜。小时候都是妈妈在院子里讲故事,满天繁星,那个景象现在在池上依然如此。这不仅是他们本身没有进步到工业革命之后。文茜你大概听说过,有一段时间,当地农民联署要电力公司拆掉波浪稻谷上所有的路灯。那不是为了美,是因为稻谷如果晚上不休息,就不会是好的稻谷。我本来以为他们是为了浪漫,其实不是的。所以说连稻谷都要休息,何况是人。池上产生了欧盟、日本都来抢购的优质大米,就是靠这样培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我对农民的一种敬重,就是他们很少预料到,WTO以后台湾的米价会大跌,所以他们逆势操作,往优质米去发展。现在他们的冠军米,价格大概是台湾西海岸的米的5倍。所以同一个时间里,在那边可能是非常悲情的哀叹,可是在这里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陈文茜:梁大哥在我的节目说,池上米现在已经不参加比赛,把冠军让给别人,他很客气地讲这句话。
◆蒋勋:每次他们比赛我去看,我都会吓坏。三十几种评比的内容,关于矿物质的含量等等。他们现在的冠军米大家都会立即抢购。他们的收入有15%-20%会转到一个协会,池上的孩子读大学的学费都是由这个钱在出。我意思是说,池上了不起,不只是让大家看到一个风景的美。
◇陈文茜:你说池上的孩子读大学都是这个基金会在资助?
◆蒋勋:对,池上的孩子根本不用担心将来读书的问题。我觉得好动人,就是说池上的背后绝不是我们匆匆观光看到的表层的美,它背后有很强的一种力量,让我忽然想到四个字:锦绣大地。所以我现在常常跟朋友说,池上很美,不只是自然。锦绣是人刺绣出来的,而他们的一生的辛劳在那个土地刺绣出来,劳不一定是苦,他们会有一种笃定的快乐。叶云忠他们夫妇俩在农地里耕作,他们的收入是可以跟大学教授一样的。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产业的基础。所以我说人只讲空想的东西,是不够的,还是要有一个产业上很扎实的现实,才可以满足。
◇陈文茜:你现在才碰到一个真正的左派,对不对?以前你在年那时候是另外一种人。
◆蒋勋:对,我跟梁大哥说,我就是论语里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我现在跟他们学习,到哪里我就问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然后很兴奋,觉得到这个年龄可以重新有老师非常棒,而他们就很安静。我第一次10月底住进去,然后到11月12月收割以后,一月的油菜花金黄一片,我就在旁边大叫说:「哇,美呆了!」我就画了一张画。
◇陈文茜:我们好有默契,我刚正在翻书准备要问你这个问题,你自己就讲到了油菜花。
◆蒋勋:因为那真的是金黄金黄的,然后我就在那儿惊叫。后来我看到游览车一辆一辆过来,所有台北来的人都在惊叫。到立春要插秧的时候,推土机把油菜花推倒,你就会看到台北来的少女在哭,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农民就会跟她说,那本来就是肥料,因为下一年它的稻作就是要靠这个做养分。我在旁边就有点感动,觉得我们真的离这个东西太远了。希望有一天我们在生死面前可以不尖叫,知道它本来就是一个循环,我称它为「自然秩序」,我发现自己已经离那个太远了。我们惊叫、大惊小怪,真的是因为看的太少。当地人就很安静,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们安慰那个台北来的女生的声音。我希望重新学习这个东西。
◇陈文茜:它生来就这么美,扮演一个祝福的角色,这是它的使命。当时他们邀请我到池上去,住的时间很短,那个时刻刚好是看油菜花田的时刻,稻米已经收割了,油菜花刚刚长出来没有多久,还有一些被放到餐桌上。
◆蒋勋:那个新鲜的油菜花好好吃哦。
◇陈文茜:你别一天到晚都想到吃啦。当时,我就有一个感悟,因为我知道这个油菜花它是一整片很漂亮。有些可以拿来吃,大多数就是等到最漂亮的时刻,把它翻下来,然后就开始要插秧了。后来我发现这不是只有在池上,有一天我到了长江口跟东海的交汇点,有一个地方叫南通,他们也是把整片很漂亮的油菜花推倒要种稻子。那个地方也是长寿村,当地岁的老人有个,平均年龄都是90岁左右,九十几岁的已经有一万多个人。我后来发现,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对于这些美的东西会有执着、不舍,不能理解生命的循环,而那些跟土地一直在一起的人,他会敬天,他会了解有些东西活下来的命运是什么,包括他自己。
◆蒋勋:我觉得这两年我做的功课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自然秩序,另一个是土地伦理。这两个功课,我发现在现在的教育系统里是学不到的。要怎样把孩子带到自然秩序,让他知道春夏秋冬的自然变化,不能因为我喜欢春天,就让春天留着,它一定是在变化的过程。古老的人类在自然里一直学习这个道理。而土地伦理就是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分享。我觉得做这两个功课大概是我最近最快乐的事,所以我回到画布前面,不再像过去我在寻找自己的忧伤,我会觉得他们在土地里劳动,我在画布上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劳动,只是比较安静。
我特别佩服的是,他们有很多焦虑的时候,有一次看到焚风(指气流翻过山岭时在背风坡下沉而形成的干热的风,强大的焚风可造成干热风害和森林火灾)吹起来,热度一下飙到40度左右,然后就看到梁大哥他们忧心忡忡,一直看手表。半个小时后,焚风停了,天上的火烧云也停掉了,我记得我还拍过,蓝天慢慢出来。他们就松了一口气,我问说怎么了,他们说再吹半小时,今年的收获全部变空,就会烧焦的。他们立刻到土地庙去拜拜。我觉得现在我好像可以分享池上人的丰收的快乐,我也可以分担他们在面临土地灾难时的那种忧苦,可是他们都用很平静的方法度过。所以我们在都市里吃到那么好吃的池上米,我们大概不知道背后的忧伤跟辛苦,特别是当初推广自然种法和有机种植的时候,得罪多少人,多少人简直要跟他们打架。可是他们就觉得这是一定要走的一条路,因为你一家人自己有机种植,没有用,旁边农园的农药会飘过来,水源也会污染。所以在这个公顷的土地上,有一个不得了的经验,这其中有农民的智慧跟远见,来完成这样的东西。
-END-
-商务联系-
吴小姐
wuxin
media.北京最好的白癜风医院北京哪家医院看白癜风转载请注明:http://www.meijiangwang.com/lxccp/955.html